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張艷霜(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研究生導師)
初聞《兩京十五日》改編成了舞臺劇,我腦中第一個念頭是:這很難吧?作為馬伯庸原著小說的讀者,驚訝于將70萬字的小說壓縮成幾小時的舞臺劇應屬不易。小說取材于《明史》中關于明宣帝朱瞻基的一段寥寥50字的經歷:“六月辛丑,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在善于于歷史縫隙中閃展騰挪的馬伯庸筆下,擴展成了一部情節跌宕起伏、人物眾多的恢宏小說。如今被改編成舞臺劇,也算是文藝創作者對馬伯庸歷史小說的改編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舞臺劇的魅力就在于方寸間即時性的局限下劇本、視效、聲效的巧妙編排和演繹。受限于場地與藝術表現手法,也很難像小說那樣天馬行空、反映現實,舞臺上呈現更多的具有寫意、假定性的美感,而觀眾需要調動想象力在舞美構建的歷史空間中探索細節,在燈光煙火的渲染中感受劇中人物的情緒。在這一點上,《兩京十五日》是成功的,沒有真實的房屋、山林、運河、大船,而是結合中國的山水畫、戲曲、音樂和美學,以假定性的表演呈現出山林水火的意象,展現出一種獨屬于中式美學的氣質;并且通過布景的變換及多媒體的虛實結合,實現波瀾壯闊的時空穿梭、日行千里的篇章場景。
戲曲元素是本劇最大的特色之一,演員的形體表演里融合了中式戲曲的程式來展現主角們不斷趕路、日夜兼程的敘事節奏。比如主角趕路時在舞臺上走圓場,假裝行走,以表現時空的轉換;打戲的時候利用旗子代表某種實物配合演員動作;太子被朱卜花追殺時,蠟燭滅后太子和殺手的表演類似京劇《三岔口》里的身段。最具戲曲表演元素的是對白蓮教相關角色的呈現,護法昨葉何的表演全然是旦角的做派,念白也是戲曲式的,這樣的設計使反派的角色更加鮮明,令人耳目一新,與舞臺設計共同營造出一幅白蓮教的奇幻景觀。
在劇情改編上,受到篇幅和時長限制,舞臺劇必須對原著精髓進行有效“提純”。《兩京十五日》原著小說最大的特點是細節縝密、人物生動、劇情緊張,而舞臺劇需要在3個多小時里呈現這種緊湊的敘事、輪番出現的一百七十多個角色、兩京之間兩千多里路的星夜奔馳。2021年版的舞臺劇嘗試不算成功,豆瓣評分只有5.7,多是吃了沒做好劇情取舍的虧,導致故事線散亂、人物性格平淡;沒有過硬的劇情內核,使得舞臺布景和多媒體很容易喧賓奪主,吞噬表演本身。今年導演趙淼帶領團隊重新創作,重新取舍了支線劇情,能夠較好體現主角人物的成長但并沒有脫離主線故事;重塑了人物性格,盡量還原原著中的人物性格特點。加上相得益彰的舞臺設計,個人認為《兩京十五日》作為一部商業舞臺劇,立住了。
當然這部劇還有需要打磨的地方,如敘事過于依賴念白,大量的臺詞對于演員的臺詞功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因“趕進度”而加快語速,觀眾就更加難以聽清楚。此外,原著小說中的問題也帶到了舞臺劇里,馬伯庸在小說里賦予女主角蘇荊溪其不能承受之重的人設——一個反抗封建禮教的先行者,在小說終章蘇荊溪復仇原因的揭秘部分被大量讀者視為“敗筆”,在舞臺劇里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改進。雖然其藝術化呈現較小說來說更容易被接受,但內在邏輯的虛弱依然讓觀眾感到無法融洽。馬伯庸在小說創作手記里提到他在翻閱明史時深感殉葬禮制對女性的殘酷迫害,以至于他必須借蘇荊溪這個角色代表千萬女性對這種吃人的制度痛聲譴責,這是一個有良知的創作者對于自己的寫作做出的一種取舍。但一部舞臺劇顯然無法承載這么多表達。
諷刺的是,歷史上的朱瞻基在上位后雖然締造了“仁宣之治”,但死后仍然有10位妃嬪為其殉葬,女主角蘇荊溪的訴求終究沒能實現。而這個隱晦的注腳,就藏在火燒明樓那一幕里:火光中,蘇荊溪和吳定緣反復詰問太子能不能廢除殉葬制度,而太子跪在地上,遲遲無法說出那個答案。劇尾的字幕稱頌了朱瞻基的歷史功績,卻隱去了殉葬而不表。不知這是創作者有意為之,還是實在不忍直陳這歷史細節中的人性幽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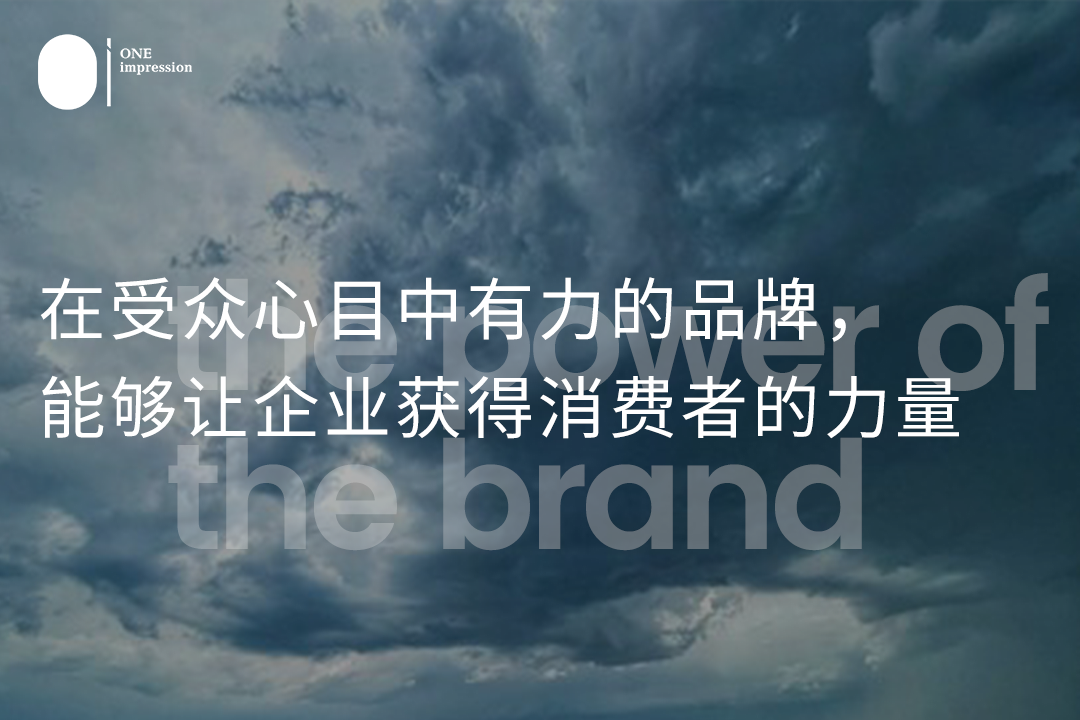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