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論壇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22》發布式——“賬戶養老金與財富積累”通過線上方式舉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張盈華在論壇上表示,關于零工經濟或者平臺企業的勞動者參保,平臺企業是非雇主,但是應當有責的,可以承擔一部分繳費或者是匹配繳費,幫助這些騎手也好,快遞員也好,去參與到第二、三支柱,甚至第一支柱。另外,我們的參保要更加靈活,既然面向的是靈活就業群體,參保要靈活,要有一些零星收入、按單收入,而不是按月繳費的方式,可以用后臺管理的方式,比如零星扣款,但是按月去匯繳到財政專戶、社保專戶里面等等這樣方式方法的創新來包容我們的零工經濟,要考慮到賬戶養老金的流動性訴求,之所以大量的儲蓄變不成養老金資產,就是因為養老金資產腰背鎖定到退休,對于很多具有流動性訴求比較高的群體來說,要考慮賬戶的鎖期要適度,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去提取,并且有一些歸還的要求和不按時歸還的懲罰,這樣適應零工經濟人群的需求,讓我們的賬戶更有吸引力,打造零工經濟友好型的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以下為張盈華發言實錄:
謝謝韓老師。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又在一年一度的盛會和大家見面。我這次匯報的主題是從一個特殊群體——零工經濟的勞動者,通過賬戶養老金的制度完善這樣一個特殊群體有效覆蓋的一些思考。
零工經濟從國際看,它是一個界定,國內也有像靈活就業、平臺經濟從業人員、平臺經濟勞動者,還有新就業形態等等。有很多概念是相重疊的,但是它們有一個共性就是去雇主化。在去雇主化這樣一個情況下,怎么能夠解決對他們的有效覆蓋?我想賬戶是一個很好的載體。我想從這個角度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考。
我們國家的個人賬戶在三個支柱里面都有體現,但它們的功能是不一樣的,在第一支柱個人賬戶目前有很多爭議,主要是在個人賬戶的定位上。比如說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曾經就有過地區試點個人賬戶,比如說海南采取“大統籌、小賬戶”的方式,深圳采取的是“小統籌、大賬戶”的方式,這兩個試點后來被采納的是一個,相當于是一個中間模式,我們在1997年的時候,按11%的費率來界定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后來在2001年因為要做實,就縮小了做實的比例,個人賬戶的劃入費率是8%,一直持續到現在。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他們對個人賬戶的屬性劃分是不一樣的,海南幾乎把個人賬戶看作是私有的,所以要做小,而深圳認為它是基本險中的一個部分,承認它是一個公共屬性,盡管它是大賬戶,但是它是一個公共的。關于它是私有的還是公共的,學界其實是有不同看法的,到現在也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共識。
在1999年財政部的一個報告里面曾經提到過,說基本險的個人賬戶余額是不可繼承的,實際上也是在認可它的公共屬性,因為它要共濟。但是有很多學者提到說個人賬戶的空賬實際上是在挪用個人儲蓄性資產,認為個人賬戶是強制性的私人養老金,可以劃入到第二支柱或者第三支柱等等這樣一些看法。對于個人賬戶不同屬性的認知,實際上是決定了大家在研究第一支柱個人賬戶的時候對于它的規模大小、去留問題,是虛賬還是實賬等等,大家的出發點就不一樣。
我們一直在考慮用名義賬戶這種給付的計發辦法來改善我們的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用它的自平衡機制來改善這種個人賬戶,實際上就是認可它是一種公共屬性的,對于這樣一種認知也就決定了個人賬戶能否劃入到第二或者第三支柱的一個基本的前提。早晨我們也聽到有建議說把個人賬戶的一部分劃入到第二或者第三支柱去做實我們的私有的個人賬戶,就是第二、第三支柱,有合理性,但是也需要認真一點,目前我們國家的第一支柱,也就是公募養老金個人繳費只有8%,單位繳費長期以來是20%,現在降到16%,即使降到16%,雇主的繳費依舊是雇員繳費的2倍,這和很多國家的繳費比例是不太一樣的。有的國家是一半一半,有的國家是甚至于雇員繳費比例更高,大多數國家至少雇主是承擔了2/3的繳費,雇員還要承擔1/3的繳費,我們國家如果把個人的繳費部分從第一支柱劃走的話,實際上相當于弱化了個人在第一支柱的繳費責任,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學術問題。
在第二支柱里面,我們一直關于第二支柱的定位,它的這種理念還是有一些困擾,有一些困境,是什么呢?是因為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的起源是從企業補充養老保險這個身份出現的,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探索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當然它是由于國企改制,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改變,出現了降低企業責任,降低政府責任,所以那個時候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前提就是企業有能力、有意愿自愿建立,所以在最初的一些研究,甚至認為我們在基本險替代率比較高的情況之下是可以不用考慮擴大企業年金規模的。在2001年的時候,我們那個時候有將近6%的單位,非私營單位的就業人員實際上是加入到了企業年金的,現在這個比例已經提高到了25%,但是在基本險的參保人數里面,我們這20多年,實際上它的比例提高并不是很明顯,從2001年的不到5%提高到現在不到9%,從這樣一個比例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這20年大量的參加企業年金的依舊是以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為主,這樣一個制度實際上是對私營單位或者說今天說的零工經濟人員并不是很有包容性。
在企業年金制度建立的時候,2004年試行辦法出臺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政策規定,就是加入企業年金的前提必須要加入到基本險,這樣的話就是把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捆綁起來,加入第二支柱必須要以加入第一支柱為前提,不僅要加入,企業還要按時足額繳費,這對于很多有意愿想要加入的中小企業或者是個人來說,它是有一定的困難的,或者是有一定的制度上的限制,這是需要我們去考慮的一個問題。
在第三支柱上面,關于個人養老金的定位是一個補充式的還是一個替代式的,如果是一個補充式的,疊加福利,提高它的待遇保障,世行專家曾經也是將第三支柱或者叫第三層次,認為它是高收入者獲得更高收入替代的一種制度安排。但是如果要是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的話,前提必須要有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保障,然后在上面再累加,這對于我們今天說的零工經濟從業人員來說也是存在著一定的困難的。所以個人養老金的這樣一個賬戶是否應該是一個疊加的屬性,在制度設計上面是否把它看作是更高的收入保障的一種追求,還是需要重新考慮,至少從層次角度考慮,也應該從支柱角度考慮,這樣我們才能把零工經濟的人群納入進來。去年中國勞動學會有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者里面有超過1/3的月收入是低于5000的,是不夠個稅標準的。還有近一半的是在5000-7000元的范圍,如果把這樣的零工經濟從業納入有能力繳費、可保障的群體,或者三支柱體系有效覆蓋的這樣一個群體里面,我們現在必須要考慮他們的這樣一個繳費的能力、繳費的意愿以及制度的包容性問題,如果他們沒有力量參加第一支柱,又沒有一個雇主參加第二支柱,當然他就沒有意愿參加第三支柱,所以第一支柱過高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的雇主化的這樣一個要求,可能就擠出掉了第三支柱的發展。這是一個關于三支柱的認知。
對于零工經濟如何參保也有很多國外的探索,我這里列舉了一下,也寫在了報告里面,比如自主加入且自主責任。英國在引入自動加入機制的時候就認為個人是對個人的繳費負有全部責任的,個人對你增加養老儲蓄是負有全部責任的。還有一些國家是強制注冊的,比如說烏拉圭,他們允許這些零工經濟人員在他們的手機App上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平臺企業不去承擔這樣一個雇主責任,你自己可以去繳費,這個是強制注冊的手段。還有用合同約束雇主責任,比如說南歐國家,像西班牙、意大利,他們明確這種Uber司機和平臺具有雇員雇主關系,所以對雇主責任是通過合同或者法律來約束的。還有一種是使用者付費,就是你在購買這種東西的時候要多付一部分錢,作為零工經濟從業人員參保繳費的費用來源,相當于誰是購買者誰來承擔這樣的雇主繳費責任,當然他不是雇主。還有一種是按單自動扣繳及由平臺企業配比繳費或者分擔籌資責任的。這也是國際勞工組織所倡導的方式,還拉美國家的方式。
這些國家的這樣一些探索對我們考慮零工經濟人員參保也好,他的保障也好,都是有啟發的,至少有一點啟發,就是賬戶的這樣一種載體是很有用的,不管是強制的也好,自主的也好,不管是使用者付費還是雇主匹配付費,都是通過賬戶這種方式來實現大家的這樣一個資金的匯總,實現參保資金的來源。這是一個啟發。
我們國家零工經濟者如何去參保?如何去納入到這樣一個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里面?需要了解零工經濟從業人員的就業特征。國家信息中心公布的共享經濟發展報告里面提到,2020年我們依托互聯網就業人數8000多萬,其中僅滴滴平臺就1000多萬,但是他們的認勞率都非常低,就是沒有什么勞動合同,很多零工經濟人員認為他收入不穩定,所以是斷保的主要原因,這是他們工作的特征。如果把零工經濟也納入到整個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里來考慮的時候,可以看到,如果將他們納入進來是有多重好處的,對個人而言可以平滑生命周期的消費;對于社會來說,可以避免收入保障風險聚集,因為很多零工經濟人員都是參加的居民保,居民保一旦他們退休的時候,他們的待遇將會和職工保中間的基尼系數可能會非常大。而這種差距可能會成為將來社會的一個新的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或者是一個火藥的點,一個爆發的點。對于整個經濟來說,將就業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的零工經濟也納入到我們的這種保障的體系里面,可以避免他們的就業歧視或者就業排斥,職業身份的這種排斥。比如說網約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這兩大群體天然的對立,就是因為一個繳社保、一個不繳社保,一個是正規的,一個是不正規的,一個是有雇主、有平臺、有靠山的,一個是完全靠自己的,這兩類群體這種身份的不同、成本的不同,也就導致他們競爭中間并不是平等的,出現了很多職業的排斥或者身份的排斥。對于我們這兩類群體之間的磨合,邊界給它模糊化,實際上有利于經濟形態的融合。
最終我提一些建議,怎么去發揮賬戶養老金的制度效能對于零工經濟人員的包容性?首先我有一個認知,消費型的福利過大就相當于竭澤而漁,我們高福利國家只給你發錢,躺在福利上,收入關聯性的福利可能只是授之以魚,讓他有退休后的保障,但是資產性的福利是讓大家有一個不斷增值的機會,所以應當考慮把零工經濟也納入到資產性的福利制度里面,讓他們有資產、有養老的資產,而不僅僅是有一個將來收入的保障,基礎的保障。
我們看一下我們國家三個支柱之間的關系,在1997年的時候,當時統一養老保險制度目標替代率是58.5%,這個大家都知道,個人賬戶要承擔38.5%的目標替代率,到2005年目標替代率提搞上去了,到59.2%,但是個人賬戶承擔的目標替代率降到24.2%。之所以確定這樣一個目標替代率是考慮到我們要把當時比較高的替代率,尤其是1997年制度剛建的時候,那個時候平均替代率是超過80%的,80%的第一支柱替代率降下來實際上是為第二、三支柱留下空間的。到現在確實是降下來,可是我們的這種降下來是一種被動的,是由于養老金的增速沒有工資增速快而產生的這種被動結果,并不是我們提前提早讓利出來給第二、三支柱,所以,我們現在替代率降下來了,第二、三支柱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第一支柱的擠出對于第二、三支柱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它的替代率比較高,相對來說比較高,沒有讓渡出這樣一個空間,或者說讓參保人更多地依賴在了第一支柱上面。這是我們目前的問題。
對于這三支柱,我們要考慮要進行一種探索,我認為應該是一種系統觀的探索,不能單說第二支柱,也不能單說第三支柱,我們要把一、二、三支柱放在一起。所以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如果第一支柱的替代率不降下來,第二、三支柱是發展不上去的,從長遠考慮來說,第一支柱的替代率可能要加速降低。第二支柱的壯大,在考慮自動加入的時候,還要了解中小微企業的需求,因為我們現在自動加入一定是面向的是這一撥群體,而不是大型企業,大型企業已經納入進來了,所以要考慮中小微企業的需求,要從多層次需求的角度設計多層次的自動加入機制。對第三支柱來說,除了一個億的納稅個個體,我們要把他們納入進來,還要考慮未來我們還有一些沒有在這個納稅群體里面,那些零工經濟人員,那些低收入的,相對低收入的零工經濟人員應該用什么樣的差異性的政策引導措施將他們引入到這樣一個制度里面。
所以賬戶一定要設計好,如果設計不好就可能成為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有人說它是新瓶裝舊酒,因為現在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完全和繳費年限掛鉤,就相當于計劃經濟的時候是以工齡掛鉤的退休制度,沒有改變計劃經濟的這樣一種習慣思維,這種路徑依賴依舊是存在的,不僅缺乏這樣一種公平,也沒有效率,比如說它又是一個公有的公共的資產,但是它又可以被繼承,又缺乏這樣一種激勵的參保,如果制度設計不好的話,將來可能會要,我認為可能必然這個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是要進行改革,甚至是要重塑的。第二、三支柱產權是比較明晰的,但是賬戶的效率還沒有發揮出來,比如說怎么把儲蓄變成資產?怎么讓它更便于攜帶?怎么能夠適度?我大概粗略地算了一下二、三支柱,我們國家的稅優力度已經不亞于美國401(K)和IRA合在一起的稅優力度,為什么我們不能撬動大家去參與呢?就說明我們這種稅優的制度和我們的參與人群之間還應該有一個更好的匹配性,如何增強二、三支柱賬戶的吸引力等等都是需要市場和政府的智慧的。
最后提一點建議,關于零工經濟或者平臺企業的勞動者參保,首先我們認為平臺,我說的是平臺,就是2021年當時界定的,三分法界定的第二類群體,他們沒有辦法確立勞動關系,但是又和平臺有一定的被管理的這樣一種關系的時候,我認為平臺企業,至少這樣一種群體,他是非雇主,但是應當有責的,可以承擔一部分繳費或者是匹配繳費,幫助這些騎手也好,快遞員也好,去參與到第二、三支柱,甚至第一支柱,如果我們的制度是包容他們的話,這些企業非雇主,但是有責任去匹配繳費。另外,我們的參保要更加靈活,既然你面向的是靈活就業的群體,參保要靈活,要有一些零星收入、按單收入,而不是按月繳費的方式,可以用后臺管理的方式,比如零星扣款,但是按月去匯繳到財政專戶、社保專戶里面,等等這樣方式方法的創新上來包容我們的零工經濟,要考慮到賬戶養老金的流動性訴求,之所以大量的儲蓄變不成養老金資產,就是因為養老金資產腰背鎖定到退休,對于很多具有流動性訴求比較高的群體來說,我們中國人不光自己花錢,我們還要對家人、給子孫后代都要花錢,這個流動性的訴求非常高,要考慮賬戶的鎖期要適度,要有限地可以去提取,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去提取,并且有一些歸還的要求和不按時歸還的懲罰,這樣適應零工經濟人群的需求,讓我們的賬戶更有吸引力,打造零工經濟友好型的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
以上是我的分享,不對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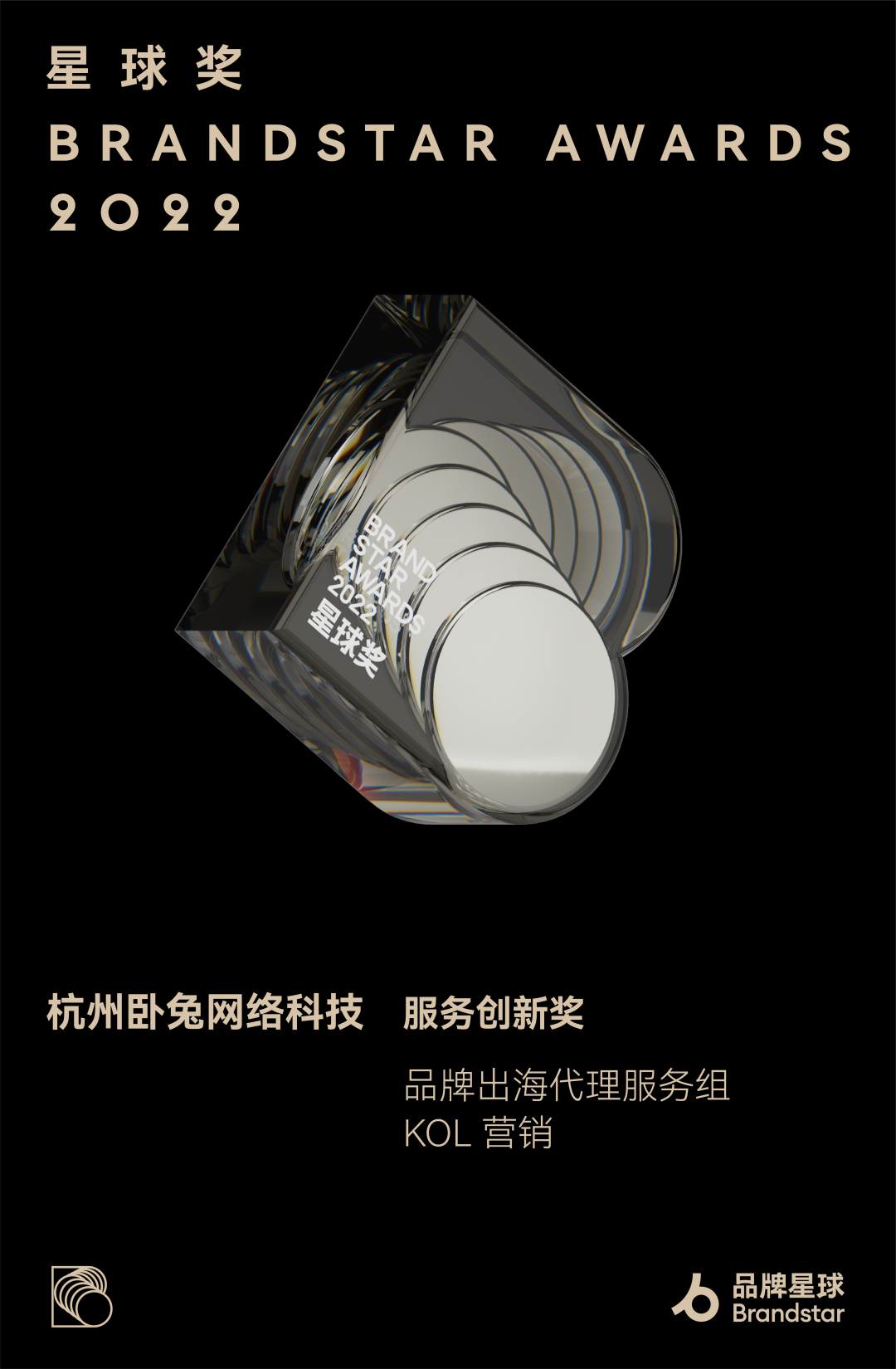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