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論壇暨《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22》發布式——“賬戶養老金與財富積累”通過線上方式舉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執行研究員高慶波在論壇上表示,人口結構擺在那里,而且被長期低估了,所以從更長期來看,個人養老金前景必然可期。但是短期內我個人持審慎態度,發展過程并不一定一帆風順。而且最后一個感觸是由于第三支柱或者個人養老金制度的制度框架剛剛構建,現在還處于大范圍試點階段,所以我個人預期是未來制度仍處于完善進程中。公共養老金制度繳費率和待遇之間是否能達到平衡,繳費率能否繼續下降,這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二、三支柱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尤其2006年以后,怎么樣把他們做聯動是一個問題。
回應前面鄭教授的那句話,我們的目標是怎么樣能構建一個覆蓋更多人的制度。公共政策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一種排序,我們怎么樣能為更多的人群提供更好的保障是我們目標所在。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以下為高慶波發言實錄: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
大家下午好!
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點感悟。領到任務的時候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類似于雜談的東西,因為我預期到很多東西前面各位已經講到了。我的主題想從認知偏差談起,做下前景展望。
內容包括三部分:認知偏差是什么、多層次體系中的目標定位、最后做前景展望。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東西?今年4月份的時候7號文發了,咱們國家從1991年提出來的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的目標到今年4月份制度真正意義上的框架才算是確定,7號文做了很大的變化。從1991年提出多目標層次以后,1995年的時候,套用世行說法是第一支柱公共養老金制度基本提出,1997年算是正式確立。第二支柱2004年已經確立了,企業年金制度,2015年、2016年加了職業年金,采用同樣框架體系。第三支柱就比較困難了,一直到有稅收優惠的制度試點是到2018年開始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剛才標的時候它真正的意義是什么呢?第一次引入了EET模式,因為在各界很多年一直呼吁引入EET。所謂EET就是三個環節:購買一個環節、持有一個環節、領取一個環節,每個環節是否免稅,在最后一個環節收稅的時候,各界一直在呼吁,有很多文章介紹了優勢,2018年這個引進來了。但是當時有兩個非常大的限制:一是僅限于商業保險公司。二是它是依托于企業的制度,必須有企業單位參加參保,7號文是什么樣的變化呢?一是范圍大了,稅優模式還是采取EET,但是稅收優惠幅度從7.5%變成3%。二是不再僅限于商業銀行,銀行、理財公司進來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事情它不依托于企業了,因為它要求的是只要你參加了基本養老制度,兩種哪種都可以,換句話說它把依托于企業的限制拿掉了。最后有一個新的東西就是在企業年金制度里缺失的個人選擇權加進來了。
在這樣背景下,我看到了很多特別樂觀的預期,那時候想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討論第三支柱也好,討論個人養老金制度也好,我們可能有很多大家都很熟悉但卻被經常忽略的問題,從平均預期壽命談起。過去很長時間里,無論第二支柱期間,還是誕生之前,包括到現在,這20余年間,關于各種類型賬戶制度規模預測的文獻很多,通常切入點有:一是國際比較,國際是水平,中國是什么程度,做個比較。二是談當前制度缺陷,當前制度存在什么問題,怎么完善。三是從人均預期壽命。大家來看澳大利亞精算署的生命表中,澳大利亞精算署在2010-2012版里面關于預期壽命做了特別明確的總結,反思了在過去125年間,他們到底因為忽視率死亡率改善造成了多少預測偏差,澳大利亞生命表最早是在這里,1895年的時間,當時預期壽命是45,再往后看,假設這個人活到了45歲以后,排除掉各種計算誤差,我們當然零歲預期壽命和特定年限的預期壽命不一樣,但是剔除掉這個誤差之后,澳大利亞精算署得出的結論是整整低估了6年以上,大概6.8歲是被低估的。那中國預期壽命,我們并沒有那么漫長的人口統計,這是2001年五普平均預期壽命71.4歲,2010年74.83歲,2020年77.93歲,大概每10年提升3歲左右,這樣的估計偏差是人口學界里不會被忘記,但是在我們做養老分析的時候,這是常常被忽略掉的一個東西。而公眾的時候做預測的就是另外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我們在各界做預測的時候,學界也好、政府也好,它看到的是滯后的數據,而公眾的認知滯后的幅度就更大。我在這里沒有列一個文獻,我記得在2011年的時候,世行豪斯曼先生總結了OECD的經驗,里面有一個結論說盡管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OECD國家已經老齡化現實存在非常嚴重了,但是人們認識到老齡化的現實存在是在20余年以后。在我們這個領域人非常熟悉,那時候只要一提起哪個國家要宣布提高退休法定年齡了,伴隨的新聞基本上哪國群眾上節抗議了,這就是實際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老齡化的現實存在一方面被低估了,但另一方面公眾對它的認知又嚴重滯后于真實水平,而這個制度本身是基于公共個人的認知來實現的。
我們經常會說的一句話是意愿是行為的前因變量,那么認知決定意愿。每個人在符合他的認知水平里做出決策的時候,出現滯后是非常難以避免的。
從這個話題延伸出去,另外一個主題是我們經常會包括一個制度的時候忽視另外一件事就是資金其實是一個池子,我們今天討論的都咱們國家繳費型養老金制度體系,世行、國際勞工組織等等很多國際組織提倡的是多支柱、多層次的繳費體系,但是無論怎么樣把這個制度服務的提供者怎么拆分,三個支柱其實就是不同的養老服務提供者給你做的東西,但是職能沒有變,因為目標都在后面,保障老年待遇。換句話說,在所有時代里面,對于每個個體而言,這些錢都是在當代消費中扣掉的成本,而這些成本是天然存在上限的。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制度面臨的討論其他的制度發展的話,必須看作一個整體看,我們先看第一個例子,這就是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生物收益率的概況,這是我用變形艾倫條件做的東西,我們來看看平均工資增長需和制度內人口增長,我們會發現幾乎絕大多數年份制度內平均貨幣工資增長率兩位數,剔除掉這些年制度內人口增長向下的趨勢,那什么樣的回報可以在過去的時代超越它?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來自個人賬戶制度的競爭。剛才的部分講的東西非常輕,就是收益統籌部分。那個人賬戶嗎?2015年記賬利率很低,到2016年以后有一個非常高的收益率,記賬利率是8.31%。8.3、7.12、8.29,在同一個時期內社保基金收益率,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養老保險部分投資回報在這里,歷史回報率很高,這是另外一種的競爭。下面的兩塊部分一支群體問題也好,年金部分也好,前面有很多老師講過了。收益差異我想特別強調一句的是,收入差異本身不光決定了參保者的范圍有限,而且稅優的模式本身就意味著扣掉生活成本第一支柱之后,當前的稅優政策其實并沒有惠及到他們,他能參加的可能性相對比較小。那么這里特別再提一句的是后面的兩個東西,三支柱強調短期內面臨著要理順制度內部關系問題的另外一個根源在于我們2022年的7號文實際上把制度的層層疊加的制度還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制度作為了一個問題放在了這里。如果它沒有能力參加城鎮職保的話,參加了城鄉居保+第三支柱也是一種選擇,他會不會這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在這樣情況下,公共政策又應該怎么做?
既然是從認知偏差談起,大家也會很熟悉,這實際上是行為的路子。那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個點在這里,因為按照行為經濟學的觀點,它的收益率有兩個部分組成,人們應該有尋求長期穩定預期的心理和付諸實踐的預期,這個地方稱之為心理收益率。那我們按古典經濟學模型算出來是實際收益率,把這兩個部分疊加,如果大于真正決策利率的話,那實際上可能產生參保行為。這里附帶一個例子,就是當前壽險參與者顯然是可以證明心理收益率存在的。在我們國家現在制度框架下面的情況下,我建議是和大家比較接近的,加入什么呢?既然有了個體選擇權,期待服務提供者們提供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產品,并且簡化決策歷程。我們都知道在2006年的時候美國PPA法案引入了自動加入機制,自動加入了以后,大家面臨最大的問題和我們現在制度當前困境是一樣的,投資選擇權開放了,但是你面對一大框的產品,那么2007年美國打了一個補丁就是合格默認投資工具(QDIAs),這兩個制度變革也就是21世紀以來,可能在OECD國家最主要的趨勢。
不要把目光只放在EET上,中國現在的制度框架天生就是TEE,尤其是那些無法享受稅收優惠的群體,EET對于他們而言相當于征收了一個非常高的管理費,顯然他們是不愿意參與這樣的制度,那么怎么樣可以把這個制度的群體做大才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
人口結構擺在那里,而且被長期低估了,所以從更長期來看,每個人終將為自己負責,那么個人養老金前景必然可期。但是短期內我個人持審慎態度,發展過程并不一定一帆風順。而且最后一個感觸是由于第三支柱或者個人養老金制度的制度框架剛剛構建,現在還處于大范圍試點階段,所以我個人預期是未來制度仍處于完善進程中。公共養老金制度繳費率和待遇之間是否能達到平衡,繳費率能否繼續下降,這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二、三支柱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尤其2006年以后,怎么樣把他們做聯動是一個問題。
回應前面鄭教授的那句話,我們的目標是怎么樣能構建一個覆蓋更多人的制度。公共政策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一種排序,我們怎么樣能為更多的人群提供更好的保障是我們目標所在。
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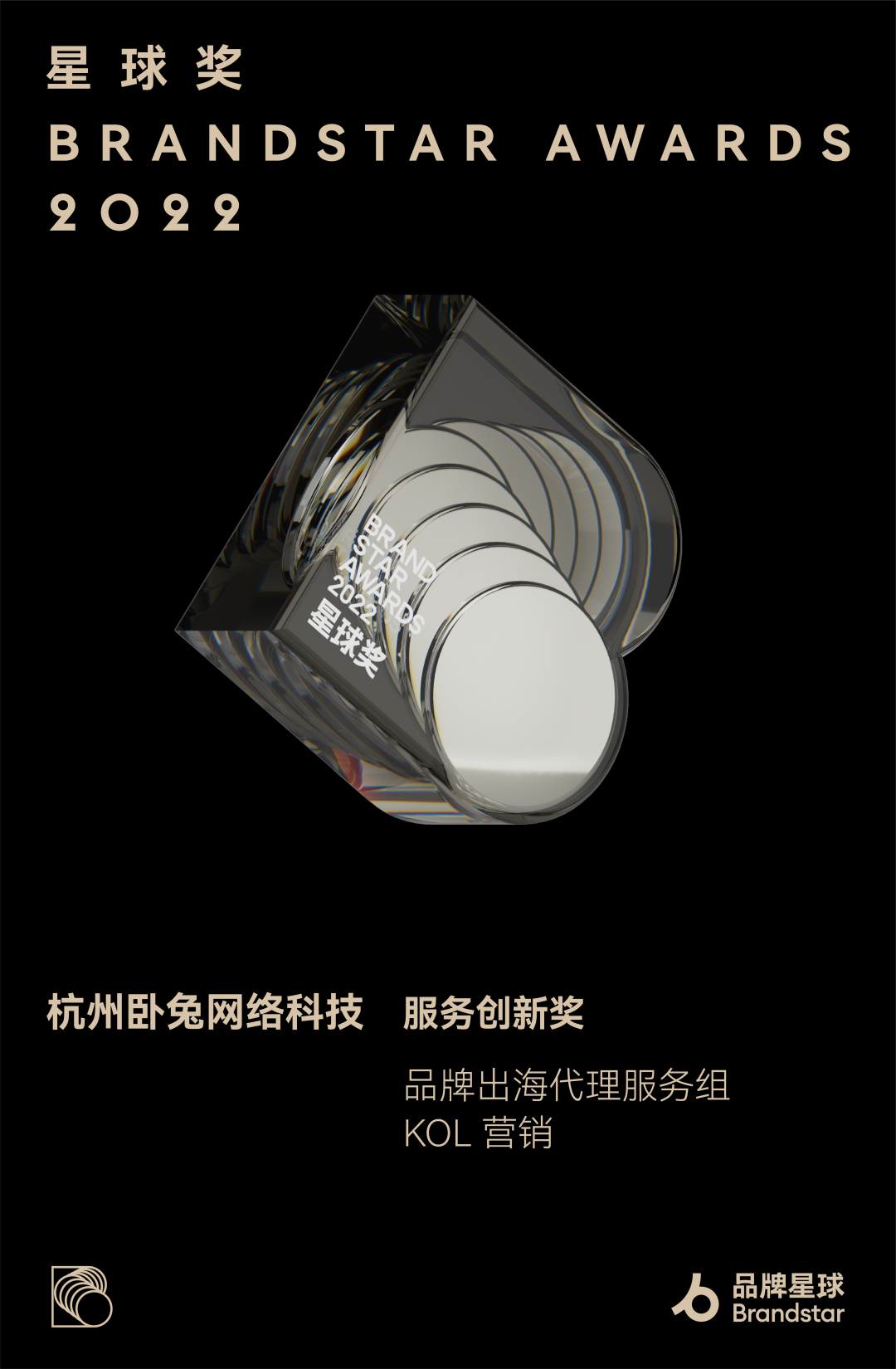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