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常德原創文藝獎獲獎作品:
蘭芷探幽
 (資料圖)
(資料圖)
——新世紀洞庭湖區域文學論
夏子科 張文剛 等著
沅有芷兮澧有蘭
——當代常德地方文學創作論略(代序)
文/夏子科
如果說,從“洞庭”“沅澧”“武陵”“湘西北”一類地理名詞中氤氳、蒸騰出來的“泱泱乎魚米饒足之鄉”①氣象更多地連接著一種鄉土歷史,表述著一種古老田園經驗或牧歌人生的話,由“大湖股份”“金健米業”“環湖生態經濟圈”等當代語匯所勾勒、描畫的“今日常德”圖景則顯然具備了極為清晰的現代指向,表明了一種新的世紀關聯與生存品格。這樣的變化,必然會在建立其上的文學形態中得到反映,同時,也必然要影響到創作者們的精神氣質與藝術思考:既眷戀,又悖離;既放縱,又內斂;既寧靜,又躁動;既充實,又渴望;既聆聽,又諦視;既固守,又超越……而所有這類復雜的情感態度與智性選擇又無疑都緣于一種愛——對置身其間、與自己血脈相連、休戚相關的文化母土和現實家園的一種本質之愛。
一、小說:“敘述有意味的故事”
新世紀以來小說界的“繽紛”和“熱鬧”似乎不大容易能夠贏得常德那群“寫手”們的注意,甚至連周邊的“文壇岳家軍”、湘西作者群及省城“湘軍”余勇們也較難形成吸引。倒不是因為感覺遲鈍,也并非有意閉塞視聽,實在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敘述有意味的故事。這也并不等于說別人的故事就沒意味,只能說各自的意味應該是各不相同的,或者說,每一位作家都應該通過一種故事積極尋找和努力散發真正屬于自己意念中的那種意味。
具體來講,小說家應看重和追求的是故事、意味和敘述三者的和諧一致,而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就是那種由故事及其潛藏的意味所鑄就的樸素的質地,所謂“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②。“有些小說家對敘述技巧的熱情過了頭,他們癡迷于技巧,而疏遠了故事本身”,此一做派,常德的小說作者們是不以為然的,他們否認有所謂“不要故事的小說”存在。同時,故事還不是目的,它必須承轉引自某種意味,“故事具有意味,也就具備了小說品質;小說故事缺乏意味,就沒有魂魄,沒有靈性,就難成其為小說,尤難成其為好小說。”③從這類認識出發,常德的小說創作開始了對意義——或即所謂“意味”的追尋。
這種意義,就其基本屬性來講,是那種融會、流貫在具體創作中的精神集合或意識形態凝結;就其蘊涵而言,則是指凝聚在故事中的生產生活理念、思維方式、情感態度、風物習性等具有地域風格特色的精神文化現象;就表現形態來看,主要是通過流溢在生活與人性本來中的先楚文化遺留,表達一種歷史追思和時代追問。
人們的觀念中,楚文化實質是因“巫鬼”而靈異,因“淫祠”而浪漫,因“南蠻”而邊緣,這實在是某種歷史誤會與文化錯覺。事實上,先楚文化是北方中原文化與江南“蠻夷”文化的奇妙的結晶,是夷夏混一,而其主導部分、其內核應該是那種勤懇務實、剛健有為的華夏農業文化。這一點,盡可以在楚人那種“老家在中原”的北望情結中,在先民們篳路藍縷、墾荒創業的生存習性中得到證明,同樣,也可以在今天的文學創作中得到證明。
最典型的實證也許就是少鴻的長篇小說《夢土》(《大地芬芳》)。這部洋洋70萬言的作品,是“唱給田土的深情戀歌”④,也是對一種母土文化及鄉村個性的認同與皈依。湖湘山地的陶秉坤,雖然比不了關中的白嘉軒作為家族長老的風光威嚴,也不具備白嘉軒那樣作為鄉村儒者的雍容高貴,但是,他的辛苦遭逢卻更能引發實實在在的生命感動,更富有人化意義與民間意義,也更能代表一種大地品格和楚文化精髓。這是一位背負著太多傳統約束與生存擠壓的標本式農民,是一個穿越世紀的文化精靈。他活了將近100歲,一生的憧憬和追求就是希望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其間,幾乎每一次喜悅都緣自土地的魅力,幾乎每一次打擊都令他燃起對土地更熾烈的渴望。最后,他終于在人極之年,在田土中央,在快樂冥想與極端自足中安詳地老去。想不到,這樣一位勤勉、艱難的普通農民,一生守著無宗教的時日,卻有著那樣美麗的宗教歸宿!他使人們不能不相信:失去土地,便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依據,也便失去了家園和歸宿。少鴻之外,曾輝的《財女》、《情中情》、吳飛舸的《淚土》等長篇及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說也體現了大致相似的固守與拷問精神。
說到“蠻”,常德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歷來是很吃得苦、“霸得蠻”的,屈原是這樣,蔣翊武、宋教仁是這樣,林伯渠、丁玲、翦伯贊是這樣,未央、昌耀是這樣,水運憲、少鴻等也是這樣。這是一種極其儒化的“蠻”,其本質應該指向一種勤勉精進,其內涵則是一種較真和執著——較真得有些迂闊,執著得近于頑固。 這是由龍舟運轉引自過來的精進較真,是由楚辭喂養成熟的勤勉執著,是一種風骨、一種血脈,她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所以才使得有的人居然能從楚辭中天才地讀出“反腐倡廉”⑤主題!看過蔡德東的《陰雨天》,你一定會強烈地體味到生存艱難中演繹著的人間溫情;看過老戈的《嘟嚕兒》及羅一德《叢莢井的故事》,從唱漢劇的“老嘎”和校總務“宋澤”身上,一定能感受到平常人生中綿延著的生命感動;看過歐湘林、白旭初的小小說,一定會發現簡單樸素中的真實深刻;看過少鴻的長篇《溺水的魚》,“尤奇”對生命和諧的執著追求會讓人感佩不已……還有兩個很有“意味”的短篇:滿慧文的《艾艾》、李永芹的《轎二》。“艾艾”“老板娘子”這兩個女人以身家性命為武器向無愛的人生展開搏擊,目的就為了維護一個女人的完整性——對愛和尊嚴的完整擁有,這中間顯然纏綿著一種真精神、真性情——那種固有的“蠻”文化個性。
二、散文:“帶著村莊上路”
的確,整個常德就是一個“水氣淋漓”的村莊,“良田,綠樹,雞飛狗吠,炊煙繚繞,都氤氳在一派水氣里。”“村莊里的物與事,每一個人,一條狗,一棵樹,一片禾場,都有自己的名字,個性和故事,都跳躍著自己獨特的色彩。”⑥這樣的一方水土養育了自己的文章,這樣的文章也把一方水土帶向了遠方。
這里,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文化個性。與先楚文化流韻、屈宋辭賦傳統內質接近而又更早形成的,還有善卷文化。史傳上古堯舜時代,沅水之陰(枉渚)的枉山(后改稱德山)孤峰嶺上,隱居著一位名叫善卷的高蹈之士,因為積善行德,帝堯曾拜他為師,舜甚至要將帝位禪讓給他,但他堅辭不受:“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藪”,遂成就一種善德文化⑦。這種文化不同于一般所謂避隱文化,其實質應歸屬于儒家倫理文化范疇,是一種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的和諧期待,一種民族道德精神與民族性格淵源。千百年來,德山蒼蒼,德流湯湯,善卷的道德精神早已內化為一種集體規約,轉化為一種民間日常倫理實踐。 接受著這一善德文化形態的濡染、燭照,平凡的生命才沐浴著一種溫煦幸福,才帶來了普通而真切的生命感動。少鴻常常期待著這種感動(《感動》),“一不小心”就在城里某個角落的那些盲人算命子那里體會了這種感動——感動于這種常常被忽略的生命也悄然滋長著綿綿執著的愛情,感動于他們雖然瞎眼而內心卻那樣的空明澄澈,感動于那種“拄杖依欄”“像發出天問的屈原”似的形象以及“一種平和、從容、專注的笑”、一種“寵辱不驚,物我兩忘的神情”!在“漫過了一九九八年夏天”的那場洪水中,母親把漂來的一捆稻草毅然推給女兒,自己卻被洪水卷走,從這里,少鴻又一次感受了一種母愛的偉大(《水中的母愛》),體會到“水中的母愛,比大地更真實,比許多的真理更像真理”。碧云則從“慢慢游”車夫那里,明白了“錢這東西,能讓完美的人更完美,使殘缺的人更殘缺”的道理(《慢慢游》)。看來,“這個”水氣淋漓的“村莊”里那些物事、人事及其所特有的樸素中的真實、簡單中的深刻,已經成為永遠的散文母題。 作為歷史文化的一部分,這里,也有令人沉醉的風物名勝。比如,桃花源里可耕田的寧謐安適與柳葉湖的嫻靜翠碧(解黎晴《走在千古騷人的身后》《乘舟看柳色》)、水府閣的恢弘灑脫與招屈亭的傲岸堅定(彭其芳《水府閣眺望》《情系招屈亭》)、夾山寺的幽曠清寂(王蔭槐《夾山覓蹤》)、花巖溪的輕盈靈秀(少鴻《白鷺之憂》);令人釅釅至于微醺的擂茶(少鴻《桃源識得擂茶味》)、令人饞涎欲滴的風味小吃(王瀘《津市風味小吃》)、令人蝕骨銷魂的辣(羅永常《悠悠辣椒情》)等就是代表。面對這樣的“村莊”,不由得你不心下戚戚、默然神往。
這里,還有作為母土與家園的浪漫溫馨。就這一意義層面而言,“村莊”已漸次模糊了最初的物質形態而被粘附了更多固守色彩與形上思考。正如盧年初所體味的那樣,“我開始把村莊像糖一樣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脫口而出(《帶著村莊上路》)。”村莊的一切都是那么輕盈美麗,萬物皆靈,即事可文:“故鄉的樹……顯得拘謹、謙卑……它們才真是故鄉的魂靈”(《故鄉的樹》);“男人的魚腥味是把年味帶進來了”(《鄉里的年味》);“往深處聽去,仿佛有鍋碗瓢盆碰響,叫你頓生回家的念頭……平原深處,一片蔥蘢樹蔭下,屋舍儼然,恰是我忘不了的家”(修客《澧陽平原》)……同時,對這個村莊本質之美的固守實際上也就是表達了某種對抗。“這世界并不像我現在所處的橘園這般滿目清新,空凈幽爽,而是隨處可見浮塵滾滾,霧氣漫天……稍一不慎,霧就可能淹沒人身體里兩件寶貝:心和靈魂。”⑧這里所體現的,恰恰是一個“村莊”對于那些出門人、對于時代的胸襟與關愛。
三、詩歌:“鮮嫩的蘑菇長出來”
關于詩歌創作,也許有必要提一提代表常德的那塊“文化招牌”、那一堵“以常德古城幾千年歷史為縱軸線,以當代中國最高水平的書畫藝術為橫斷面……準確反映常德古城的風采和現代常德人的精神風貌”⑨的“中國常德詩墻”,畢竟那上面也鐫刻著當代常德的部分詩作,但這樣的文化工程顯然還不是常德詩歌的全部。
與小說作者們的態度有所不同,常德的詩人們同外部詩歌步履保持了協諧一致:既現實過,也現代過;朦朧過,也新生代過;先鋒過,也實驗過,態度十分合作。不過,他們畢竟又不是天外來客,作為屈宋的后人,其創作內質仍然同自己母土文化根柢及家園現實存在之間有著無法割裂的精神糾結,由此也培植、生長了自身藝術個性。其創作發生,恰如詩人楊亞杰在她的詩集《折扇》中所表露的那樣,“一天又一天/日子層層疊疊/堆成形狀怪異的/記憶的小山……山的周圍/一些鮮嫩的蘑菇長出來/頂破憂郁的心情……有位荷鋤的小矮人/常常奇跡般地出現……向你捧出/語言的金子”,所以,藝術創作的靈感不會憑空降臨,“鮮嫩的蘑菇”“語言的金子”當然也不能隨意在別人的園地里采摘和攫取。
從楊亞杰那里又可以得到這樣一種啟示:詩歌來源于一種詩性態度,而這也是作為一名詩人的必備素質。以這種態度去體味記憶的窖藏、聆聽現實人生,便時時會碰撞出詩意的發現。如果進一步細分,又有所謂主觀、客觀兩種態度。從主觀的詩性態度出發,就會有對生活本然或人性本來之上的詩性贈與,或者說賦予本然形態以詩的意味,楊亞杰、龔道國等大抵屬于這類主觀詩人。從客觀的詩性態度出發,就會有對本然形態固有詩情畫意的索要,而所謂本然就是一種客觀在場,修客、周碧華等基本屬于這類客觀詩人。當然,一般情況下并沒有這樣嚴格的區分,尤其就具體創作來講,兩種態度常常并不是不能相互融會的。
于是,一種詩性的土壤與詩性態度便“長出”了繽紛的詩的意象和美麗的思辨的花朵。在修客看來,汨羅江一直深悔自己成全了一個無謂的悲劇:“屈子/你何必像離弦的箭/懷念那把棄你的弓……如今花開如月/五谷豐登/詩人/別為那楚王朝神傷”(《汨羅吊古》),這到底是修客在勸慰屈子,還是屈子在告誡修客呢?在《夾山寺獵蹤》的高立,滿心期待著能找到闖王的“轟轟烈烈”,無奈只覓得一種“把失敗的成功垂名青史,卻把不敗的正義修煉在廟宇”的喟嘆!所幸的是,在常德的土地上“長出”的這類天才造句,如今已過洞庭、下長江,同那些優秀的物產一道“暢銷”海內外了。
稱詩為“鮮嫩的蘑菇”或“語言的金子”是很恰當也很精妙的:無需太多修飾,里外皆見質地,一如真純大方的靈魂,總是那樣毫無愧疚地裸露著!這其實也提出了一種要求:詩歌創作應盡力屏棄矯揉造作,避免“做詩”。真正的好詩是樸素的,是能指豐富、內涵深刻的。就詩的語言來講,一定程度上需要充分發揮漢語表意的靈活性和伸張力,但過于隨意和不確定,將是蒼白的和十分危險的!龔道國的詩歌創作數量多,也寫出了不少好的篇章。周碧華、修客等詩人寫詩并不多,卻都是觸摸靈魂的好詩,比如周碧華《祥林嫂》中就寫道:“沿著悲劇的線索/我再一次走到魯鎮的小河邊/這條江南的小河/外表比魯四老爺還斯文/可是!祥林嫂,你不要靠近/一只白篷船藏著滿艙的陰謀/停泊在岸邊已有幾千年……”短短的幾句話,掀開的卻是縱橫幾千年、且至今仍潛藏在社會的人性的各個層面的一縷惡的幽魂,可謂擲地有聲、撼人心魄!借此我們在矚望著常德文學或即整個環洞庭湖區域文學的未來!
(原文刊發于《文藝爭鳴》2004年第5期)
注釋:
①(清)應先烈:《常德府志序》,涂春堂、應國斌主編《清嘉慶常德府志校注》(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頁。
②[梁]劉勰:《文心雕龍·風骨》。
③少鴻:《敘述有意味的故事》,《水中的母愛——少鴻散文選》,遠方出版社 2002年5月版,第150頁
④魏飴:《唱給田土的深情戀歌——就<夢土>致作者少鴻》,《理論與創作》 1998年,第2期。
⑤吳廣平注譯《楚辭·后記》,岳麓書社 2001年4月版。
⑥王躍文:《與一個村莊的告別》,盧年初:《帶著村莊上路》,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⑦善卷事跡在《莊子·讓王》篇、《荀子·成相》篇、《呂氏春秋·下賢》篇、[民國]鐘毓龍《上古神話演義》等文獻中均有記載。
⑧龔道國:《穿過大霧·自序》,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1年6月版。
⑨楊萬柱:《城市文化: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湖南社會科學》 2002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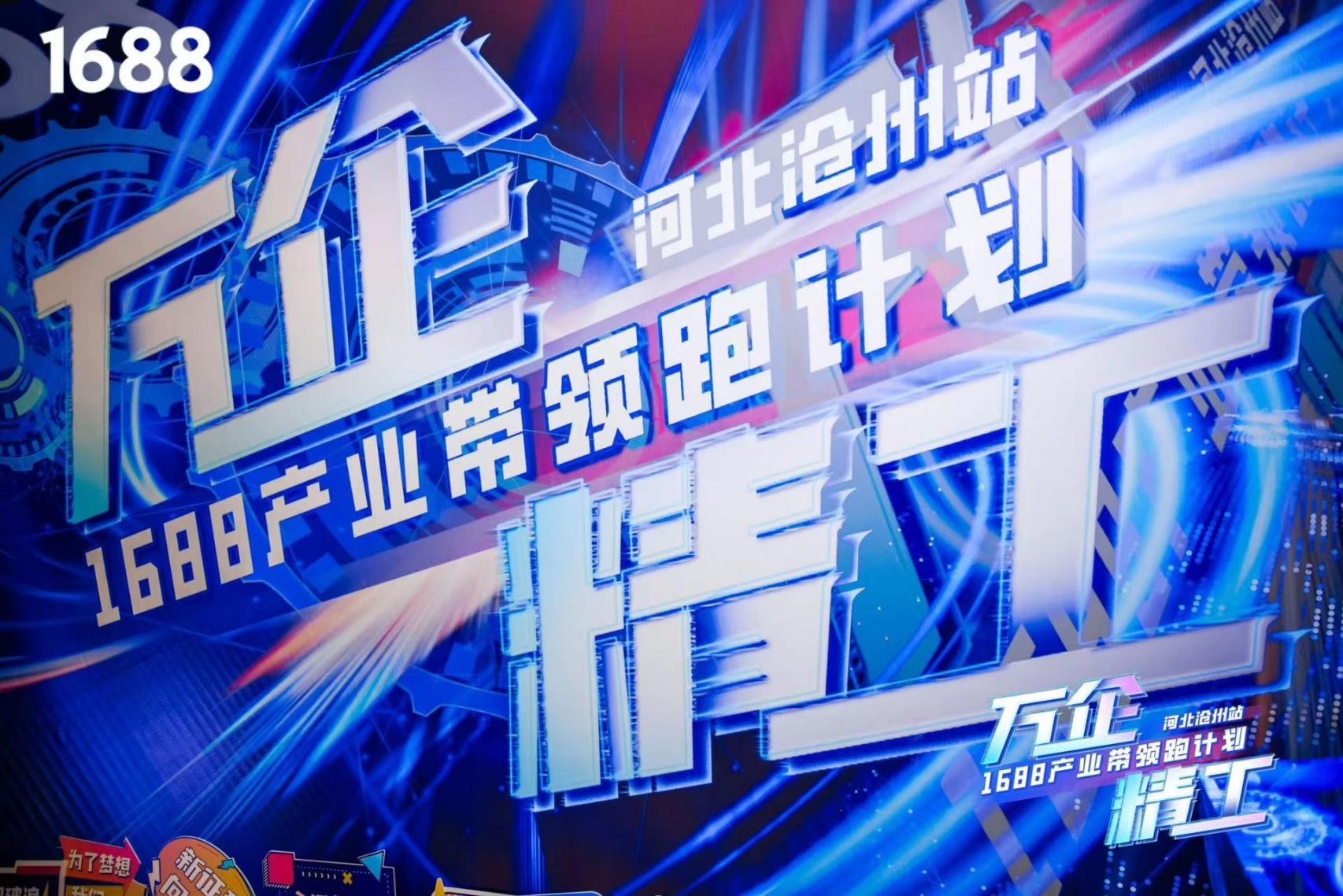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